在商周青铜器中,有一个平常很少有人注意到的类别:弄器。山西青铜博物馆中展出了数件弄器,以小型器为主,大约认为这类做工精致、与鼎簋尊卣等常见礼器有别的青铜器是日用器的一种,平时供贵族把玩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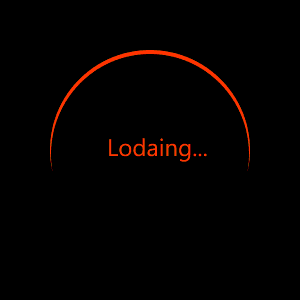
山西青铜博物馆中的展板
如果凭当代的目光,这些小型器确实很容易被当做陈设、装饰品,唐兰说这种弄器“皆指宝物之足以供玩赏者,异于寻常服用暨祭器、明器之类也”,几乎成为定论。黄铭崇观点与唐兰类似,李零则说“弄器,当与吃喝玩乐等奢侈享受有关”、其特点“一是常在手边把玩,不是供在祠庙;二是赏心悦目,观赏性强,有时胜于实用性”,都强调了它的非实用性。
但是关于“弄器”的问题并没有就此全面解决了。再仔细审视这个问题,会发现它可能很有再探讨的必要。
(一)小型器就意味着弄器?
弄器是什么样的青铜器?有一种看法,认为弄器就是比正常尺寸更小、难以完成应有功能的小型器。比如在山西青铜博物馆中陈列的弄器,均为精巧细致的小型器: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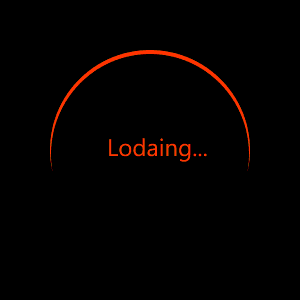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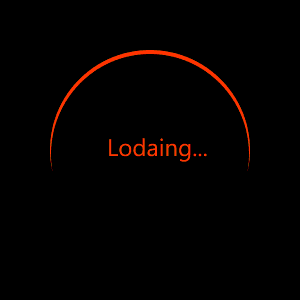
窃曲纹醽,春秋,闻喜县上郭墓地27号墓出土,山西青铜博物馆藏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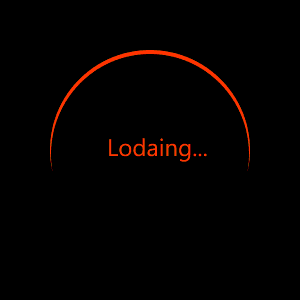
四轮方盒,春秋,移交,山西青铜博物馆藏
目前被认为是弄器的青铜器,除了子乍弄鸟尊之外,最著名的是从陕西韩城梁带村发掘出土的一组六件“弄器”,包括镂空方盒、双层方鼎、贯耳罐、圈足匜、单把罐、小鍑。它们被摆放在东侧棺椁之间靠近墓主头部的位置,青铜礼器则置于椁室西南角,可见其与常见的礼器有别。发掘者“因器形甚小,做工精致,推测为墓主生前玩弄之器,故以‘弄器’称之。”(见《陕西韩城梁带村遗址M26发掘简报》)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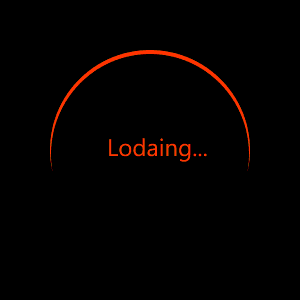
双层方鼎、贯耳罐、,图片来自《陕西韩城梁带村遗址M26发掘简报》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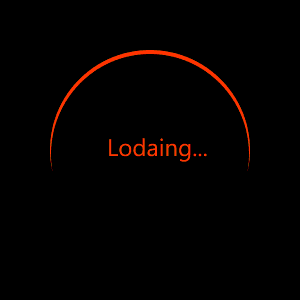
圈足匜、小鍑,陕西韩城梁带村遗址M26出土
还有一些研究者认为青铜弄器就是娱乐性质的青铜器,比如兰娟在《先秦制器思想研究》中认为“子作弄鸟”尊和“子仲姜盘”都是弄器。在用子仲姜盘“作盛洗接水之时,使用者不仅可欣赏到生动的造型,还可把玩拨弄,无疑充满了活跃的生活情趣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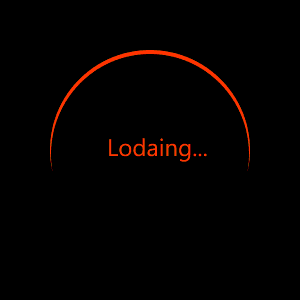
子仲姜盘,现存于上海博物馆
那么,这些器物是不是在商周时期就作为弄器呢?这要从青铜的自铭来看。
李零在《说匵—中国早期的妇女用品:首饰盒、化妆盒和香盒》(《故宫博物院院刊》,2009年第3期)一文中梳理了目前发现的、自铭带“弄”字的器物,总共列出10件。虽然有个别遗漏,比如1987年安阳郭家庄东南殷墓还出土有一件自铭有“弄”的簋(口径14.2、通高10.6,比正常尺寸偏小),但这不影响李零对弄器作出的判断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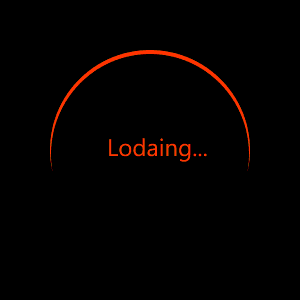
图片来自《1987年夏安阳郭家庄东南殷墓的发掘》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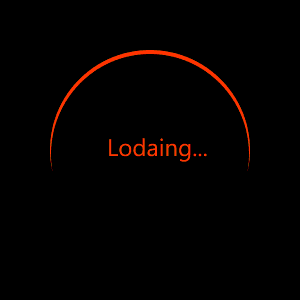
图片来自《1987年夏安阳郭家庄东南殷墓的发掘》
李零把他所列出的十件器物归纳为四组:第一组为殷墟所出两件器物,很可能出自同一人之手,这是商王所作;第二组是洛阳所出的两件天尹铃,可能是东周的官员所作;第三组是一件鲜虞(铭文作“鲜于”)的器物,做工考究,在铜壶中属于正常尺寸;第四组是知氏(晋六卿中的知氏)之子的器物,除了“君子之弄鬲”略小,其他都是正常尺寸,比如天尹钟“与一般的铃大小相似”,著名的子乍弄鸟尊高为26.5厘米,与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前期(弓鱼)伯墓等地出土的鸟尊相比,并不算小。“君子之弄鬲”,通高14厘米,宽18.4厘米,口径15厘米,这个尺寸是大于山西青铜博物馆展出的大多数弄器尺寸的。
李零列出了两件自铭有“弄”的智君子鉴,这两件铜鉴均制作于春秋战国之际,1938年出土于河南辉县。器型相同,规格相似,这两件智君子鉴应为一组。一件藏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,高22.8厘米,口径51.7厘米,一件藏于美国明尼阿波利斯美术馆,高22.2厘米,口径51.5厘米。如果根据尺寸而把规格较小的青铜器归入弄器类,那么想要把玩这两件体积不小的青铜器,不但不方便,而且很吃力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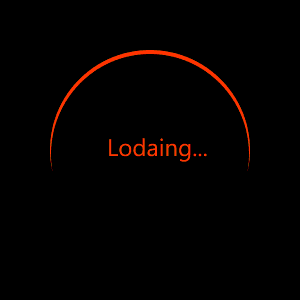
智君子鉴
也就是说,自铭有“弄”的器物其实可视为正常大小。因此李零说,“弄器可能包括很多小器物,但小不一定是绝对标准”。从上述的铭文有“弄”的器物看,大小与是否为弄器没有关系。
(二)弄器不是祭器、礼器?
唐兰认为弄器是“足以供玩赏者,异于寻常服用暨祭器、明器之类”,这并不是无端猜测。自铭有“弄”的青铜器中,有一件李零认为来自鲜虞的器物: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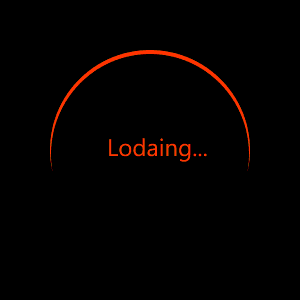
这件春秋晚期的提链壶被称为杕氏壶,铭文为:“杕氏福□,岁贤鲜于,可(荷)是金契(?),吾以为弄壶。”郭沫若认为这四句“意谓杕氏岁时贡献于鲜虞,得此金属之瓶,故以为弄器焉,而刻辞于其上,用知壶本鲜虞之器。”此处的“弄”常被解释为玩赏。因为《左传·定公三年》中说“君以弄马之故”,这里的“弄”即为玩赏。李零还说,“铭文提到‘弋猎毋后,纂在我车’,说明它是拴在田车上,供田猎游乐时所用的壶。”
这样看来,作为玩赏所用到壶,就应该脱离礼器职能,只是闲暇时把玩清赏。但从目前发现的自铭有“弄”的青铜器来看,却无法证明弄器完全与祭祀无关:
第一,1975年河南安阳小屯村出土的弄器盖(邹芙都称为方觯盖,见《铜器用途铭辞考辨二题》),长6.3厘米,宽5.2厘米,出土位置在一座殷代地穴式房子F11的内部祭坑中。根据发掘报告,祭坑长宽约0.8、深1.08米,弄器盖位于祭坑中的人骨之下。在F11房间内还出土有玉双龟、玉鳖、石鳖等(见《1975年安阳殷墟的新发现》)。要说这件器物与祭祀无关,是玩赏之物,恐怕说不过去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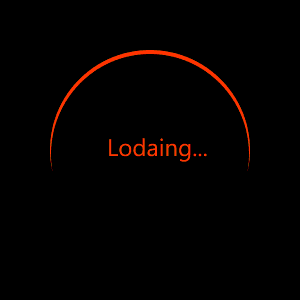
F11平、剖面图,图片来自《1975年安阳殷墟的新发现》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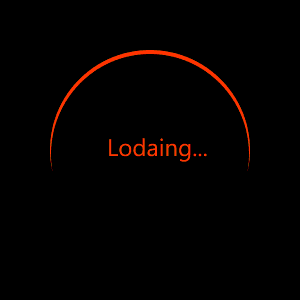
1975年河南安阳小屯村出土的弄器盖
第二,“王作□弄”卣,旧藏美国纽约的收藏家手中,高20.2厘米,其尺寸和纹饰与商代末期的其他铜卣相似,没有明显差别。商代是神灵崇拜氛围极其浓厚的时代,这种造型、纹饰也具有神圣性,通常不可日用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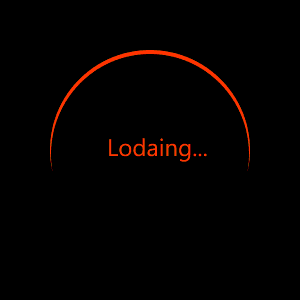
“王作□弄”卣
第三,1987年安阳郭家庄东南殷墓出土的自铭有“弄”的铜簋,簋内有一块动物肩胛骨,同出的圆鼎、方鼎、小方鼎等青铜器中也都有动物骨骼,在发掘报告中将其归入“铜礼器”内。(见《1987年夏安阳郭家庄东南殷墓的发掘》)这有力地说明了自铭有“弄”的青铜器同样会具有礼器功能。
邹芙都还提出,铜剑等是为时人赏玩收藏之物,但恰恰在繁多金文中未见有铭“弄”者,这也从侧面证实“弄”器非为把玩之器。总之,认为“弄”器是为供欣赏玩弄之器、与祭祀无关的观点,还需要再斟酌。
(三)“弄器”或为“奉器”
倘若否定了弄器体积偏小、适合把玩,以及弄器不用于祭祀,属于日常生活用品这两个观点,似乎弄器就缺少了自己明确的内涵——弄器的特征是什么,怎样的器物才能作为弄器,又回到了一片迷蒙的状态。
事实上,对弄器的这种困惑一直都在,各种讨论时有进行。唐兰固然认为弄器即玩器,王人聪却认为,鸟尊、杕氏壶和天尹铃及智君子鉴均为举行祭祀、宴享等典礼所用的礼器,决非供赏玩之物,为“珍惜”、“珍爱”之意,“弄壶”、“弄鉴”即是“宝壶”、“宝鉴”。 邹芙都则根据自铭有“弄”的青铜器中有多件“君子”之器而提出,“弄”有“珍”、“宝”之义,“弄”器为礼乐重器,“弄”器的用途可能与时人为修德而作的宝器有关。邹的观点主要为以下三点: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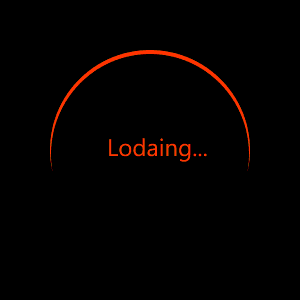
天尹铃,传出河南洛阳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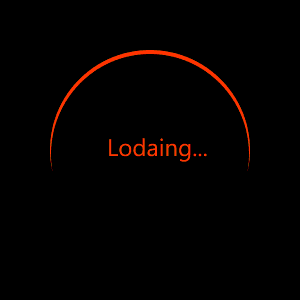
上海博物馆藏天尹铃
第一,“弄”,从玉,玉因其质地优良及产量稀少,从新石器时代以来便被视为珍宝,成为财富地位的象征。弄、玩、珍、宝均从玉义近,具有珍宝之义,此从王子聪之说。
第二,弄,“从廾持玉”,双手奉玉,以示虔敬。自铭有“弄”的青铜器中多有“智君子”之名,过去常认为是智君之子,“君子之弄器”之“君子”为“智君子”之省略,邹芙都提出君子当是贵族之称,并非指智伯的儿子。“君子”有德才能配位,因此,“弄”器的目的是修德。
第三,各种自铭有“弄”的青铜器均为礼乐器,“器以藏礼”,《礼记·礼器》:“礼器,是故大备。大备,盛德也。”意即礼犹如修身器具,通过礼器的使用,以达盛德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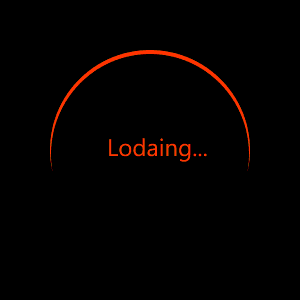
子之弄鸟尊
邹芙都得出的结论是,“弄”器可能与修德敬德有关。这不失为一种新颖的观点,也有助于将对“弄器”的理解从玩赏之器的旧说中解脱出来。但这种观点仍然是有瑕疵的,对“君子”这种人格的强调、对人的道德属性的重视,主要出现在西周建立之后,并未风行在商代。以修德敬德作为弄器的功能,又该如何解释商代的那三件自铭有“弄”的青铜器呢?
李零说,“弄”字,古代训话,解释很一致,不是“玩”,就是“戏”。弄器,当与吃喝玩乐等奢侈亨受有关(见《说匵—中国早期的妇女用品:首饰盒、化妆盒和香盒》)。不过如果追溯到甲骨文和金文中,“弄”则未必就指吃喝享乐。比如下面这幅图片上的卜辞,通常释读为“其烄弄”(合集32288),“烄”的字形像人在火上,可以理解为一种焚人以求雨的祭祀活动。那这里的“弄”显然与享乐无关,而有非常郑重、非常神圣的意义。何宏波因此说,卜辞中的“弄”字“象双手玩持玉器之形,《说文》曰:‘弄,玩也’,后世多以弄为玩赏之物,又称弄器,显己非其本义。”(见何宏波《先秦玉礼研究》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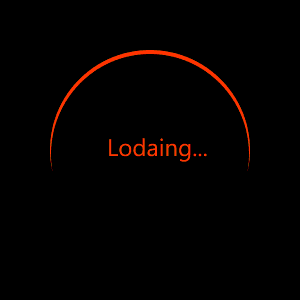
既然《说文》所认为的“玩”不是“弄”字的本义,而是引申义,那么,“弄”的本义是什么?
商承祚在《说文中之古文考》中认为:“弄字金文凡三见,一鸟尊,二杕氏壶,三即此钟(按:天尹铃)。弄当为奉之本字,言其形从一从玉,言其义,两手奉玉,有兢业敬慎之意。……三器制作花纹皆精美,决非玩器可知。”马叙伦也说,《诗经》中的载弄之璋、载弄之瓦即奉璋奉瓦。李孝定认为,“奉从丰”,“象草木形,与玉绝异,”“丰”的甲骨文字形与“玉”的字形相差太多,因此否定了商承祚的观点。汤馀惠则指出:“商代甲骨文玉字作丰、羊等形,西周金文通作王。”这就肯定了商、马(以上见李圃《古文字诂林》第三册,上海教育出版社,2001,第196-197页)。
商承祚所见自铭为“弄”的器物只有三件,目前已经增加到十余件,但他所指出的“弄为奉之本字”仍然适用。那么,这些青铜器上的“弄”就是应当供奉、贡献之意,“天尹作元弄”就是“天尹作元奉”,“吾以为弄壶”是由于此壶为杕氏岁时贡献而得名,“君子之弄鼎”就是“君子之奉鼎”,“智君子之弄鉴”就是“智君子之奉鉴”,“子之弄鸟”就是“子之奉鸟”——至于这些鼎、鉴、鸟尊是奉献给神灵还是先祖,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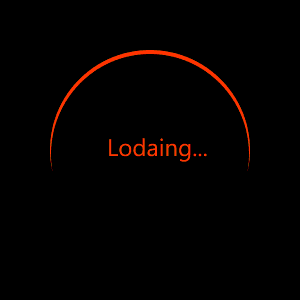
君子之弄鬲,图片来自故宫博物院网站
(四)结论
根据所出土的自铭为“弄”的十余件青铜器进行考察,结合对先秦“弄”字的分析,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:
所谓“弄器”,即“奉器”,为贡献、供奉之器,与通常所以为的“常在手边把玩,不是供在祠庙”不同,除了杕氏壶等个别情况之外,它应当是作为礼器使用的,其供奉对象为神灵之类。
同为礼器,弄器与其他青铜器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异,所谓体积更小、观赏性更强这种观点是靠不住的。除了铭文以外,想通过各种标准把弄器从青铜器中划分出来,成为一种单独的青铜器类别,恐怕难以实现。
以上为本人管见,还望方家指正。





